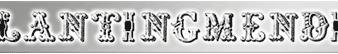|
肯定《兰亭》的主要论点
1.肯定其文字
(1)到底王羲之应该写的是什么样的字体?是隶书还是楷书?应首先搞清楚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,他说:“秦俗书为隶,汉正体为隶,魏晋以后真书为隶,名同实异。”真书即楷书,可以肯定王羲之平时写的是楷书,只是当时还叫作“隶书”罢了。楷书是后人为了区别隶书而改的“名”,唐朝大约还没统一叫法与名称。对《兰亭》持否定态度者认为王羲之处于“隶书时代”,是写隶书的,至少还是存“隶意”的,而《兰亭》是脱尽“隶意”的梁陈书体或是“唐人体段”,因此不可信。李文田是这样看,凡否定《兰亭》者基本上都以此立论。
到底王羲之书体是否脱尽“隶意”,什么叫“隶意”,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在过去的“论辩”中还没有论清楚,有待于进一步探讨。可以归纳说,肯定《兰亭》者认为王羲之“变隶为新”,写的是新体,不会是隶书,《兰亭》书体可信,这是王羲之功绩的一种见证。
王羲之所以能在书法史上被誉为“书圣”,是因为他在书法上有巨大贡献,绝非虚名。他是一个时代的“创新者”,“集大成”的代表人物。如果他只是写汉隶、章草的能手,就是写得再漂亮、再标准、再有个性,大概至今也称不了“书圣”。王羲之的功绩还在于他将汉末三国以来以钟尧为代表的(略带隶意的)“八分楷”完善化,集大成为(不带隶意的“新隶”)楷书;他的功绩还在于他把尚有隶意的章草变革为“今草”(在汉末张芝的基础上变革);把行书(在汉末刘德升的基础上发展)成熟到完全“楷化”的境地。《兰亭》便是他这种“行楷”的代表作。
近代著名学者、书论家、书法家康有为的名著《广艺舟双楫》虽有偏颇,仍不失为书法名著,其中康有为很有见地地说:“真楷之始,滥觞汉末”。肯定了楷书起于汉末三国,那末,东晋的王羲之写楷书还成什么问题?!
(2)肯定王羲之是写楷书的,其行书必然是“楷化”的。《兰亭》可信。 在书体变革时代的王羲之兼擅新旧诸体理应不成问题。他生在书法世家,家学渊源,当然更有条件兼擅新旧诸体。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所集大成的“新体”是前人不可比拟的,没有的。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不是汉隶风行的“隶书时代”,具体地说,他是在继承钟尧、卫夫人的“楷隶”(或叫“八分楷”)之后,逐渐完善化的楷书的集大成者。遍观书法史,可以悟出一个规律,即:“总有集成人”。这个集成人就是代表人物。楷书由钟尧(也有传是上谷王次仲)的“初变”,又经三国、西晋,到东晋百十年的“渐变”过程,再到王羲之则是一个“突变”。“突变”即“改革为新”的集中表现。王羲之的“突变”也是书史发展的必然产物,没有“突变”就不可能有新的书体出现。从钟尧到王羲之的100多年的孕育,决非偶然。王羲之正因“创新”而被称“圣”,当是“时代为之”。
如说王羲之的字体为“二爨”或《王兴之墓志》一类方头方脑的北魏碑味,就更不对了。北魏字体也是变革隶书的产物,是不很成熟的一种楷书,它尚存“隶意”用笔。由北魏到魏碑趋于成熟,而北魏(即元魏)晚于王羲之90年;至于地处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“二爨”字体一个晚于王羲之50年,一个晚于王羲之100年,没有前者仿效后者的道理;至于后者不象前者,是国家不统一,文化不甚流通所至,隋朝国家统一了,文字,书体也就流通了,统一了;而《王兴之墓志》与王羲之同时,为什么却象北碑?一是因为东晋尚可看见北碑,二是因东晋禁止刻碑,致使工匠粗制滥造,其时墓志文多露刀斧痕,恰与北碑的粗犷不谋而合;至于说王羲之书体应象新疆出土的晋人抄本《三国志》那样多“大波脚”,也并无充分理由。
2.肯定其文章
(1) 认为《兰亭》比《临河序》得名要早,不能用《临河序》否定《兰亭》。南朝梁人刘义庆的《世说-企羡篇》中就有“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”的话,可见《兰亭》之名早在刘宋以前就得名了,李文田引刘孝标加注《世说》中的《临河序》比古本晚百年,以后者否定前者实在不能成立。《兰亭》当初没有题目,不论是《兰亭序》还是《临河序》都是后人给加的,这个题目并不足以争。
(2) 认为《兰亭》的“167字尾巴”是可以成立的;认为《临河序》的“40字尾巴”倒显生硬,文体不合,是序外的内容,不应算正文。
郭沫若先生否定《兰亭》的“167字尾巴 ”,认为它不合王羲之的思想,肯定《兰亭》者对此不服。他们认为王羲之的思想兼杂儒、释、道三家,并不是纯道家,纯老庄思想,何况人有喜怒哀乐,思想情绪中时常充满矛盾是合情合理的。王羲之既雅好服食养性,不乐在京师,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。所以“当其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”,便“怏然自足”;而当其“所之既卷,情随事迁”,又不免感伤悲怀。这种矛盾心理不足为奇。周绍良先生专门对老庄思想作了进一步得分析研究并指出:“老庄”并非一家,老子有“用世”的一面,他讲“卫生”,不谈及“不生不死”,《兰亭》中的“齐彭殇为妄作”就是典型的老子思想;晋人是崇“老”而斥“庄”的。
(3) 还有人认为是《临河序》删节了《兰亭》,如金圣叹腰斩《水浒》一样,是编者不喜欢所致。《临河序》倒像段尾蜻蜓,伤了元气。
综上所述:两个“尾巴”的“讼案”意义并不大。“167字尾巴”合理,而“40字尾巴”也不足为虑(它和《兰亭》有关,而不是正文)。两个“尾巴”哪个是注家增改,哪个是注家遗漏,无关紧要。木已成舟,不必再争,“讼案”应撤去。《兰亭》其文是可信的。
(4) 也有人认为《兰亭》中出现的两个“揽”字是王羲之避讳祖父王览的作法,这是东晋士大夫的清规戒律,这是作伪者难以周全的,因而更确信《兰亭》。岂不知智永是王览的九世孙,他是知道避讳的。以“揽”字定乾坤也不足为据。
(5) 不少人认为郭沫若先生断言《兰亭》是智永所伪托,不足信。刘汉屏先生认为出家人戒律森严,不行骗,不慕名利,智永何必伪造七世祖的手迹来欺世呢!因此说《兰亭》世“智永所伪造”的说法是站不住的。郭沫若先生说智永临王羲之《告誓文》帖后的“智永”题名,用笔结构和《兰亭》书法,完全是一个体系,从而肯定《兰亭》是智永依托(即伪托)。郭沫若先生说王羲之《告誓文》于梁代以入密府,智永不可得临。智永其人虽生卒不详,但史称“陈隋间僧人”,他不可能在梁朝临《告誓文》,到了陈朝《告誓文》是否还在密府?郭沫若先生也没提及,这种“马虎”就难以服人了。一朝一乱,“密府”又怎么样?谁说得清!清人杨宾就有类似郭沫若的一种说法。他说开皇本《兰亭》(隋文帝十三年刻本),“帖尾年月小字与智永《千字文》字体相类,似出智永。”这里很容易误解为开皇本《兰亭》是智永的字,郭沫若是不是受杨宾这种启发而推断的呢?很难说。开皇本《兰亭》由于不见于宋人著录,一般被认为是后人伪造隋代的刻本,况且翻刻失真,磨损严重,与神龙本《兰亭》相比,相差甚远,再看智永《千字文》,三者并不相象,因此,很难断定智永在搞伪造。就神龙本《兰亭》与智永《千字文》相比,差异就不小。如说神龙本《兰亭》不象王羲之,但也并不像智永。智永为何要煞费苦心地伪造一种既不似自家书又不似王羲之的“生异”之字?这样就不露“马脚”便于欺世了吗?!然而,《兰亭》文章草草,不忌涂抹,一气呵成,文书具佳,毫无犹豫与雕琢;智永有40年临书不下楼的功夫,何不平心静气搞一份文与书都酷似王羲之的作品;而去草草为之“生异”之字?搞得既不象王羲之,又不像自家书呢?!然而,《兰亭》可信之处就在于有些“荒率”自然。岂不知既要“生异”就不能“荒率”,既“荒率”也不能“生异”,二者不可兼得?!
(6) 肯定《兰亭》者认为王羲之是在跋契盛会上饮酒赋诗,微醉之后写《兰亭》,因此连干支纪年的“癸丑”二字都含糊了一下,后添上的,这合乎情理。全文还有多处修改,以及旁挎、涂抹、覆盖之处,不妨一一列出来:
第4行的“峻”字旁挎“崇山”是丢了字,可能当时就添上了。 第13行的“因”字所覆盖的是个“外”字,前一句中有“一室之内”,相对应的下文应有“外”字,匆忙中“外”字用早了,便用“因”字盖上去。
第18行的“向之”覆盖的是“於今”二字,“向之”是加斟酌后改定的,更妥帖。
第21行的“痛”字覆盖得“哀”字,原为“哀哉”改为“痛哉”更加重了语气。 第25行涂抹得两字是“良可”,后因语气不足改为“悲也”,再次斟酌,又觉“也”字不如“夫”字,故改定为“悲夫”。
第28行最后一字原为“作”,斟酌后觉不妥,因为“斯作”说不清是哪个作品,不如“斯文”说“这段文字”或“观点”更好。
以上这几处修改、涂抹,更易体会王羲之微醉之下的神情,也有可能某些改定之处是回家酒醒后斟酌改定的。
(7) 至于考证《萧翼赚兰亭》以及《兰亭》陪葬昭陵的问题,肯定《兰亭》者一般都相信这一“说”一“史” 。这里从略。
|
|

|